
革命理想高于天(油画)沈尧伊

《地球的红飘带》之一(连环画)沈尧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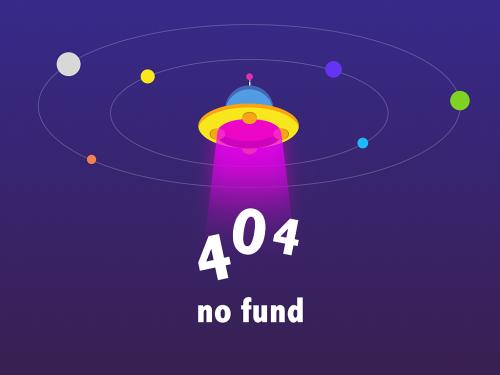
夹金风雪(油画)沈尧伊
常有人问:你为何对长征情有独钟?我答:因喜大美。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在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绘画创作中的艺术追求,那就是――视觉艺术的历史纪实。
我在创作《地球的红飘带》的时候,越画越觉得这样一段时光对我来说是非常神圣的,产生了一种编年史式的图像史诗的情结。
《地球的红飘带》连环画是根据魏巍长篇小说改编的,表现了20世纪30年代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光辉历程。1988年,我受中国连环画出版社邀约,着手创作《地球的红飘带》,历经6年,全套连环画创作完成。2016年,北京画院美术馆展出了“《地球的红飘带》连环画原作研究展”,集中展示了我为长征创作的926张原稿中的绝大部分。
连环画是文学性与绘画性相结合的综合艺术,在艺术上有极大的容量。尤其在历史纪实方面,它既能体现历史纪实风格的影片中所呈现的高视野、全方位和多层次的风格,以及编年史般的样式,同时还能充分显示绘画的造型优势。
创作历史题材,一是再现,二是表现,二者相互交融,或有偏重。我画《地球的红飘带》偏于再现,表现寓于其中。对于这个历史事件,人们是在不断记录和表现中逐渐深刻认识它的。对于后世来说,有价值的作品往往是那些比较客观和真实的作品。
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完成了第一册150幅之后,一个问题困扰着我:倾向。究竟是更版画性,概括、强烈和简捷,还是更生活化,真实、朴素和身临其境?连环画创作是不能停顿的,倾向在左右摇摆,但我最终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其结果,版画语言并未冲淡,却有了新的面貌。一种更充实的表现力,超出了我最初设想的效果。当我画完过草地一节时,连自己也像从泥泞中爬出来的感觉,我相信读者会受到感染,而语言,不被人察觉,也许是一种最好的存在方式。
长征,举世闻名,但图像缺失。我多方搜集,见到的长征历史照片也只有15张,均为当地照相馆拍摄。因为长征途中留下的史料、图像以及文献甚少,我通过重走长征路、采访长征老红军、搜集相关史料等不同方式去深度了解长征。画画的人最怕自己瞎编乱造,你脑子里能有多少东西?一定要去看实地的东西,那种味道、那种感觉,才可以通过具体的画面体现出来。
我去过川西北的草地好几次,那里早晚温差特别大,夏天也要带羽绒服,紫外线特别强,可以把脸晒脱皮,难受得很。到了那儿,人的心情也受到很深的影响,就特别能体会当年长征战士们的心情。部队的生活得问老红军,我画的时候,很多老红军都还在世,我可以问他们。但因为他们不是搞艺术的,所以对形象的东西,泛泛地问当时红军是什么样,他们说不出来,但是你可以用画图的方式来问。我画了各种各样的图,问当时红军使的什么枪,就画了各种各样的枪,我说当时你们使的步枪、轻机枪还是重机枪,他一看就说这个对,有这个,那个不行,那个太老了。我问你当时背的什么包,就给他画了各种各样的包,他就跟我仔细地讲。他是依照图的概念去给你讲的,如果用文字概念他就讲不出来,因为这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事情。
作品的意是文字,境是画,境是你看到的感觉,这个是文字写不出来的。比如说你到一个什么地点,那种味道是什么样的,你的感受是什么,然后通过绘画的合适的角度、合适的光线、色彩来表现感觉。我写生画的遵义老城,包括铺子、卖的山货,还有竹编的筐等等,那些东西特别有味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土城战役遗址,我问当地人当年毛泽东从土城到青杠坡指挥所是怎么走的,然后他们就引着我走了当年的路。其实那条路非常普通,普通到根本画画不会顾及的一条路,它是一个斜坡,斜坡上有一些仙人掌,还有一些草,有一些石头,下完雨滑溜溜的,就是那么一条路。我说我要沿着这条路走,这就是我的幸运,我沿着这条路可以走到历史里边去。
我画《地球的红飘带》特别较真,比如红军到某地开了个会,文字上就是一句话,但是画可能就得用好几张。到了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得交代,在哪儿开的会,实地要交代,大家坐在什么位置、什么样的形态,这个过程都得交代。
塑造主人公形象,首先要创造与主人公息息相关的人物群像。普通红军战士群像的塑造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主要着力于把握长征这个特殊历史阶段所赋予战士的特征。诸如,艰苦的条件与坚定的气质所构成的独特美感――南方人的风格特征,异于长征前后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特殊装备等。不少表现长征的视觉艺术作品都忽视这点,而丧失了真实感。仅举小例:红军八角帽。那种在电影中规格整齐、帽檐挺直和八角鲜明的红军帽,虽然式样上没有错误,但在视觉造型上显得虚假。在长征艰苦的环境下,帽子不可能这么规整。在回忆录中记载,徐特立在长征中就自己缝制军帽,居然没有帽檐。最重要的是,从艺术上看,新帽子没有生命,而旧帽子就可能有生命。经历了枪林弹雨,风餐露宿的红军战士,他们的艰辛从军帽也可窥一斑。整体的真实感是由细节构成的,艺术创作中只要忽视几个细节,艺术魅力就会大打折扣。
长征精神从总体说是一种思想境界的崇高美,具体而言是极其艰难的客观环境与坚定的信念、非凡的毅力的矛盾统一。视觉艺术是通过相当具体的造型来体现美的。以服装为例,画画的人都知道古代人的长袍大褂或少数民族的服装极易入画,而军装则很难画。其实这很大程度是受古典艺术那种审美情趣的影响。比如在白描《八十七神仙卷》和永乐宫壁画中那种流畅的线条,随风飘逸的衣纹和舒展的人物造型塑造了一种脱俗高雅的美感,而把这种美或者表现其美的形式技巧用在军装上显然不行。这就需要重新到生活中去开掘生活美,从而创造艺术美。红军的军装从式样说和现代军人没有大区别,但在造型上却很有特征。相对来说,红军军装显得很紧,尤其是衣纹,若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是三种衣纹的交错:一种是因为布质和长年运动留下的固定的横纹,一种是有动作时产生的活动衣纹,另外还有因为装备比如武装带等的紧勒而产生的皱褶。军装虽旧,然而风纪整齐,这种造型特征和人物质朴坚毅的气质相辉映时,产生了一种朴素美。在画家的笔下,一切都应当是有生命的,因为画中一切视觉形象都被一种审美情感所维系,这种情感具有点石成金的魔力。
为了体现“文献性”,对于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中的众多人物、场景以及环境,我都进行了全面的构想、组织和充分的展示。凡文字中提到的红军长征到过的地方,我都用一幅或两幅相连的“宽银幕”专门刻画,对于人物活动的室内外环境也有相当具体的展示,不仅不回避,而且知难而上。这些地方我都基本上进行过实地考察。每当我进行创作画到那些地方时,一种熟悉和亲切感就会涌上心头,在脑海里,这些山、水和建筑是立体的,似乎是有生命的,每每使我产生出一种强烈的愿望:把这一切尽量多地告诉读者。返璞归真是我在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创作中追求的风格。有人觉得写实的路已经走尽了,依我看这条路还相当宽阔和深远。只要生活无穷尽,把握亲切、自然、生动的生活的艺术就会长盛不衰。
《地球的红飘带》之后,我还创作了《长征交响》系列油画、《长征・1936》连环画等许许多多的长征题材作品。老实说,我是抱着“朝圣者”的心态,沿着历史留下的印痕,收集点点滴滴的视觉元素,感悟着历史之境界,在长征造型之路上艰难跋涉的。美国记者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说:“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这个史诗情结我是一直没有放下的。长征精神必将成为我们文化的一种精华、一种基因流传下去。
(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连环画艺委会名誉主席)